|
|
切除大腿上良性肿瘤的手术不复杂,做四小时左右,方明中途就醒了。他穿着绿色无菌服躺在手术台,眼皮睁不开,听到主刀医生跟护士说“再拿盐水冲洗一下”。他第一个念头是做梦,接着才有些害怕,意识到自己是“术中知晓”了。
在全身麻醉下还有意识,且在术后能回忆起的状态,就叫术中知晓。方明在北方一家三甲医院做了三年麻醉医生,去年七八月查出良性肿瘤,手术安排在今年过年期间。主任们还在放假,值班的麻醉医生和他是熟人,两人经常一块儿吃饭。
方明回忆,他当时觉得没什么可担心的,在麻醉前,还玩了一会儿手机。手术后躺在病房里,他开始向负责麻醉的同事求证,“主刀医生盐水冲洗是什么时候?”同事说,两个半小时左右。他告诉同事,自己听到了声音。
在方明的讲述中,给他做手术的同事刚来不到半年,规规矩矩按照用量,镇静药用了国产丙泊酚,肌松药用的进口顺式阿曲库铵。术后讨论时,方明和同事都觉得是丙泊酚出了问题——眼皮睁不开说明肌松药有用,醒得快说明镇静药效不佳,他解释。
丙泊酚原研药“得普力麻”10秒起效,代谢快,副作用小,能让患者快乐睡去,有个代号叫“快乐小牛奶”。它是麻醉医生用得最趁手的“一把枪”,方明介绍,全麻三要素,镇静、镇痛、肌松,镇静药首先想到的就是丙泊酚。
丙泊酚以脂肪乳做载体,有一股鱼腥味,作用是包裹药物,保存药效。福建麻醉科医生张超观察到,某国产品牌的丙泊酚静置一会儿,会分离出油脂层,张超对保存效果存疑,用前还得“摇一摇”。
之前,方明也用这个品牌的丙泊酚,他注意到病人术后容易提早醒过来。方明是住院医生,除了科研外,每天起码做5台手术。他今年26岁,本科学习药物动力学,临床两年,再读研读博。第一次遇到“术中知晓”,是一位20多岁做腹腔镜手术的女患者,那时他刚工作不久,手术一个半小时,诱导期(注:麻醉分为诱导期和围术期,诱导期指起始阶段)给药后,围术期需要持续给药维持麻醉状态。
在方明的讲述中,他用微量泵推注镇静药国产药丙泊酚和镇痛药芬太尼,维持生命体征。芬太尼属于管制药,没有纳入集采。在手术快结束准备停麻药时,方明发现病人已经睁开了眼睛。他记得术后问询时,病人说,术中一直能听到医生说话,但是她说不出话来。肚子里面能感受到压力,但没有痛觉。“可以忍受,但有点恐怖。”他转述病人的描述。
按照术中知晓的处置流程,方明给病人请了心理咨询援助,但“心里五味杂陈的”。之后,他碰到从医20年的主任医生,问如何处置,主任医生告诉他,只能增大药量——用药指南推荐2到3mg/kg的推速,以前选择2mg,现在推荐2.8mg——没超过说明书用药,也增加了麻醉的深度。
方明两年前被调派到县城医院工作,8个病人做胃肠镜手术,只有2个值班麻醉医生。他记得有一次快结束时,病人动了一下。“应该是丙泊酚药效欠佳”,方明解释,肌松药失效也会导致患者体动,但胃肠镜手术做的是静脉全麻,只用镇静药,不用肌松药。
在方明的观察中,胃肠镜手术是用到丙泊酚最多的地方。他介绍,一个成年人体重约为60到80kg,丙泊酚用量一般在15到20ml,国产品牌能维持15分钟,是原研药的一半。这增加了他的工作量,要在5到10分钟内重复给药,保证手术顺利。
这会导致另一个问题,丙泊酚有一个副作用是降血压,方明说。他给一些高血压患者输注时间过长,又容易低血压,得加强警惕,监测血压,再给一些血管收缩的药。
轮到自己经历术中知晓,方明和同事讨论复盘,只想出两点:一是“加大药量确实比较安全”;另一个是向科室建议,老人和小孩的手术增加一些监测设备。除此以外,两位新手医生也想不出其他方法。
是药的问题还是人的问题?福建的麻醉医生张超从业13年,还是没办法回答。他遇到一个35岁的女患者,体重50公斤左右,做无痛胃肠镜。一般丙泊酚最多20到25ml能麻醉倒,但这次,张超记得,用某国产品牌的丙泊酚,加到40ml才麻倒。
这个女的是不是有吃安眠药?或者抗抑郁药?是不是肝氧化酶体系有异常?或者是否长期接触到毒品?这种不对劲,他当作个体差异就过去了。
麻醉药效和个人体质有很大关系,体重、代谢不一样,对药的反应也不一样,“就像一个人的酒量,有人一点点就倒了,有人得用很多才倒”,张超说。根据每个病人的情况,医生会写一份麻醉计划书,列明麻醉方式、麻醉药的选择。药如果不稳定,就会面临“这批药是不是得多加一点”的问题。
多位医生提到,麻醉就像开手动挡的车,医生是司机,负责把不同的患者安全送到目的地,有离合、油门和刹车,重要的是“掌控”感。这两年,在一些麻醉医生和几位临床医生的感知中,失去的就是这种感觉。
2024年夏天,在福建某三甲医院工作的张超遇到一批集采肌松药,几个病人都术后明显感觉恢复意识了,但肌松没恢复,他想不通为什么,猜测是不是胆碱酯酶缺乏症?一种影响肌松药代谢的罕见病。去查病人的血,看胆碱酯酶的值也正常,他才推测,可能是这批肌松药的问题。
遇到药物起效时间推迟、出现不良反应的情况,张超也怕被同行说自己操作不专业,“因为拿不出证据,只能说这都是个人感受。”
今年初,南方一家二甲医院麻醉医生于婧第一次碰到患者体动。甲状腺部分切除手术,预估两个小时左右完成,手术刀刚划开皮肤,患者右手突然微动,当时手术开始还不到半小时,于婧回忆。
她又追加了2毫克肌松药,同时启用吸入式麻药七氟醚,用来增强肌松药的药效——于婧从仪器数据观测和经验判断,这种情况是患者意识没有恢复,而肌肉张力恢复,“肌松药代谢时间一般是在40分钟到1小时,那天在十几二十分钟就代谢掉了。”
于婧有些意外。在麻醉诱导时,她根据患者体重计算用药量,为其静脉输入了四种药的混合剂,其中肌松药用的是某国产药6毫克。在普外科医生崔勇眼里,于婧是合作多年的老手,患者手动令崔勇疑惑,“按她的经验来说,不会这么快就动的。”但崔勇也认为,偶然一例不一定有代表意义,“也可能赶巧了,或者刚好那个药确实给少了,都不好说”。
在手术室,于婧那天当众解释说,可能药是新厂家或新批号,是自己“对这个药还不熟悉”。她有些委屈,现在更多使用复合麻醉,三五种药一起,是为了缓解药效不稳定出现的新症状,于婧解释。
在过去一两年,她发现常用的丙泊酚出现注射痛的情况,开始加一些镇痛药利多卡因或芬太尼进去。通常病人不会知道,于婧会通过各种方式弥补、改善药效不稳定的情况,否则就是“我麻醉没有做好”。
在药代动力学上,国产仿制药和原研药的分子结构一致。2018年《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试点方案》出台,药品开始实行集中带量采购制度,仿制药进入集采竞标的前提条件,是通过药品一致性评价,即以生物等效性试验,证明其在质量和疗效上与原研药一致。像上述医生所察觉到的药效差异,“并不在分子结构,而是在于仿制药的杂质和纯度”,医生方明和张超都这样认为。
《红星新闻》报道指出,要证明集采前后药效的差异,只有随机对照试验能令人信服,例如2000个病人,一半吃原研药,一半吃仿制药,看对照效果,拿出数据。但在该报道中,西部一家三甲医院的药剂科主任坦言,“真正的临床研究很费钱,花精力,是个庞大的事情,我们暂时还做不到。”
在方明的科室里,一些有争议性的案例会拿到会议上讨论。他经常坐后排,把复杂难搞的案例记在笔记上,以便更好应对治疗。
相比起对药的信任,如今他更相信脑电图、心电图,血压和血样检测仪等等。他也发现,2024年更新的诊疗指南,也在强调增加一些术中监测设备,如脑电监测仪,预防术中知晓;定量神经肌肉功能检测,降低肌松残余的发生率。
麻醉医生既要满足主刀医生的需要,又要保证患者生命体征平稳。如果麻醉药代谢快,手术快结束缝合时,主刀医生会要求追加。
方明的困惑是,肌松药如果加多了,患者镇静药代谢完了,肌松药没代谢完全,无法自主呼吸,会有生命危险。他这时会加点生理盐水,回复主刀医生说,加了肌松药。他解释,这些微调是保证麻醉的正常进行,只有麻醉医生自己知道。
对丙泊酚的信任度下降后,方明才想起其他各种各样的镇静药,咪唑安定、依托咪酯、环泊酚。他会向患者推荐依托咪酯,国产药,但价格二三十块钱,药效比较稳定。或者环泊酚,10多块钱,但是新研究出来的药物,也比较稳定。
国产药并不是每批都不正常,“有时这批药不正常,下批药又正常了。”福建医生张超说。他对药效的判断主要依靠信息的流通,他记得有时科室群里会发,“最近丙泊酚药效不行,做无痛胃肠镜,可能要稍微追加剂量,不然消化科医生要有意见了。”
在东北某县城医院,麻醉医生大刘从业已有10年。他经历的都是2到3个小时的小手术,县城医院不会有太复杂的手术。近一年,他发现病人术后苏醒有些慢,再问病人是不是做梦了?很多病人说做了,这表示麻醉深度不够,大刘解释。
科室里讨论说,某国产肌松药维持时间短,他就在术中定个闹钟,不等药效过去,也不等主刀医生喊,就补一下。去三甲医院见习,那里更注重术中监测设备,做腹腔镜手术,会有虹膜设备检测二氧化碳,但在县城,没有这个仪器,大刘说,更依靠麻醉医生对患者反应的观察,看看脸色和心率的变化。
他不知道原研药,也不在乎集采药,就算药效有差异,也能“微调”——他本来也不依靠说明书,更依靠实践和感知。“最近苏醒延迟现象变多,等到再观察1到2小时,慢慢病人又好了。”对大刘来说,这是外界环境改变了,自己就像在狗窝里躺着,“不舒服了(药效变了),就用鼻子拱一拱窝,让自己躺得更舒适。”
关于麻醉药副作用的知识,他是在家里的客厅补齐的。妻子在同一家医院的ICU工作,需要更长期泵入镇静药和镇痛药,因此需要副作用小的药物。去年,妻子告诉他,一个专家做了实验,在ICU长期泵入的一种药,对循环系统的影响比较大,同时引发的副作用较多。
大刘本来习惯用这款药,听到这个之后,他开始有意识地减少使用。那时候科里出了环泊酚,他开始尝试用环泊酚替代,再按照体重年龄,看搭配的镇痛药剂量开多大,肌松药开多大,环泊酚应该开多大。再术后问问病人感受,有没有术中知晓?是否做梦?醒得透不透?
大概3个月后,他知道了少量推进后会发生什么,大量推进会发生什么,给多大的剂量,这个人他可能会发生什么,“能兜得住底”了。等到环泊酚有了不好的影响,他又开始换药。
一位湖南某三甲医院的麻醉医生称,已经习惯了集采药,觉得复合几种镇痛药物的情况下效果还可以。但她提出新的问题,药物选择面太窄。学医十余年的普外科医生崔勇指出,现在开药,被很多东西束缚住——不能老用一种药,即使觉得药效好,如果不在集采范围或者另有同类药物,会被怀疑医生跟药厂有利益关系,要写情况说明,“不是简单的当一名医生”。
另一种声音认为麻醉科面临的争议,不完全是集采药的问题。南方一家三甲医院肺移植科主任赵辉称,他操作的都是全麻手术,七八个小时过程中,至今没有发现病人提前醒来。对于国产药的药效,赵辉承认抗生素临床药效有差别,“确实不如进口的,但是这种比例很小”。器官移植术后常用的抗排异药物,赵辉比较认可国产的。
年初,国家医保局就集采药问题赴上海多家医院调研。关于“麻醉药不睡”的说法,接受调研的医院麻醉科临床医生介绍,“医院每个月平均2000多台手术,麻醉药在集采前后用法用量没有大的变化,诱导剂、镇静药、肌松药等各种类型的麻醉药都没有太大变化。”
官网内容称,瑞金医院对集采麻醉药“丙泊酚乳状注射液”的使用记录进行回顾性比较,纳入了2023年12月和2024年12月肝胆外科病区接受全身麻醉的腹腔镜胆囊切除术患者。从麻醉全过程看,原研药与集采仿制药平均麻醉药用量无统计学差异。单独看其中的麻醉诱导期,集采仿制药平均用量157mg,原研药平均用量146mg(集采药品和原研药品每支含量均为200mg)。在未发现“麻药不睡”、人均丙泊酚总用量无差异的情况下,麻醉诱导期仿制药人均用量略有增加,需收集更多数据分析研判。
对于原研药,过年前方明所在医院群发了一条通知,科室会议也强调了一次,“如果患者有强烈使用原研药的需求,或集采药的kpi完成了,可以开点原研药。”方明有些犹豫。平时,一些老人和小孩,因为体质原因,方明也会给他们开单子,让他们去医院国际部或特需部,或者直接去药店买。
但投诉也变多了。他曾给一个五六岁的男孩开处方,男孩得了急性支气管感染导致的肺炎,在麻醉插管之前,得把肺炎治好,否则会加重感染。方明解释了一大堆,小孩抵抗力差,让男孩父亲去买原研药,作用小,但被误认为是“拿提成”,闹到了医务处,要他道歉。
知名医疗自媒体“健识局“去年就报道,国际知名骨科设备制造商捷迈邦美称:考虑多款产品在脊柱国采中失利,计划将旗下的脊柱业务完全撤出中国。
捷迈是最早进入中国的骨科器械企业之一,1994年就开始在中国销售产品。2015年捷迈和邦美合并后,在中国便以捷迈邦美的身份参与市场。
当前,有关部门在大力推进医疗机构国产大型医疗设备占有率。
来看看某发达省份《关于2019年省级卫生健康机构进口产品清单的公示》,纳入2019年省级卫生健康机构进口产品目录清单的医疗设备,共计132种,试剂73种。
到了2021年,该省发布的《进口产品清单》显示,可采购进口的医疗设备数量骤减,从132种降低到46种,这意味着,国产医疗设备进口替代在加速推进。
这里允许我八卦一下,这46种获允许进口的医疗器械中,包括阴茎硬度测量仪——这至少说明两个问题,其一,相关人士对男性健康比较呵护;其二,国产设备连某个海绵体的硬度都测不准,国货当自强啊!
事实上,正如进口车与国产车在性能上存在相应差距一样,医疗器械进口货与国产货同样有差距。
下面引用医疗专业网的一篇文章,因为进口与国产质量差别较大,医院倾向于全进口,名单达23种,这里只节选几种——
1.断层DR摄影系统
国产与进口产品区别:
国内DR类产品均为普通拍片功能,无断层功能。
选择进口产品的理由 R系统在一次扫描下获得连续多层面的高清晰断层图像,应用于骨科解决普通平片检查所难以显示的复杂结构,明确诊断。对于有外固定和金属植入物的部位,可避免伪影,显示细微结构。 R系统在一次扫描下获得连续多层面的高清晰断层图像,应用于骨科解决普通平片检查所难以显示的复杂结构,明确诊断。对于有外固定和金属植入物的部位,可避免伪影,显示细微结构。
2.加速器质控设备
对直线加速器设备进行准确度控制和校准,是保障加速器安全有效运行的必备设备
国产与进口产品区别:
进口产品在测量时稳定性强,不会出现国产产品常出现的读数跳动的问题,可以更为准确的得到检测所需要的数据。而且进口产品的年平均数值的稳定性强,且不会随着年份的推移发生改变,国产产品随着年份的增加稳定性会进一步变得更差。同时,进口产品早操作方便性、安全性、故障率、使用寿命等方面均远优于国产设备。
选择进口产品的理由:进口产品准确度高,运行稳定,为保障放射卫生技术服务检测工作的顺利开展,以及患者检测的成功率、准确性和时效性,建议允许购买进口产品
3.手术动力系统
用于术中需要切割/切开、削磨、钻孔、锯开骨质和其他组织的外科手术
国产与进口产品区别:
国产产品的稳定性及持久性相比进口产品差距较大。
选择进口产品的理由:手术用器具要求稳定性、持久性高,进口产品更能保障患者安全。
需要指出的是,这篇文章列举的,均在某省进口采购名单之外。
还是忍不住再好奇探究一下,为什么某个海绵体的精确硬度的重要性,居然能超过上述种种呢?
这就造成了这样一种令人不安的现象——
在这样一个全球化时代,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得到全球化的商品服务,比如,可以赎买进口的消费电子产品、化妆品、名牌包包,大一点的超市里,也很容易买到进口的车厘子等食品……但是,进了医院,那些关涉一个人身体健康的关键医疗设备,却并不能保证是进口的。
有时候,进口医疗器械的消失,比进口药的消失可能更令人担忧。吃药这事有时候还能扛一扛,但与检查、手术相关的医疗器械,却往往能直接、当场决定一个人的命运。
当然要热爱国货。大力推进设备国产化,方向当然也没问题。问题是,国产替代进口不能只是图价格便宜,产品力也要及时跟上才让人安心。如果国产质量跟不上,我宁愿剥夺我吃进口车厘子的权利,也不愿被剥夺享受进口医疗设备的权利。
举个例子,一个医生朋友跟我说过,哪怕是外科手术动的医用缝合线,进口与国产也是存在差距的,进口的可以与身体一起融化,不须拆线,帮患者免除一次痛苦。
除了期盼国产医疗设备弯道超车(这对车技的考验非常高,因为搞不好就会弯道翻车)、快快在产品质量上超英赶美外,我能给出的建议就是,各位一定要加强身体保养,提高免疫力,最好能做到百毒不侵,不生病,这样不但能使自己少遭罪,也能为国家节约大量医疗开支。
由于部分进口医疗耗材和器械在医保政策及集采压力下被禁用或停供,多家三甲医院神经外科医生直言手术水平出现“倒退”,患者负担加重,甚至面临生命风险。与此同时,部分国际知名医疗设备厂商也宣布退出中国市场,进一步加剧这一危机。
继当局将大量进口原研药排除出医保目录后,患者用药疗效受到影响,许多人抱怨国产药“药效低”。另一方面,当局对医疗器械及手术室用进口药的限制,直接冲击手术疗效。一位三甲医院神经外科医生“许小”在社交平台发文透露,过去广泛使用的脑室引流管约600元(人民币,下同)一套,具备防逆流及金属芯,可在局部麻醉下完成微创手术,如今因医保禁用、医院停货而全面断供。原本仅需30分钟即可完成的局麻微创引流手术,现在必须改为全麻开颅钻孔,使用价格低廉却缺乏防逆流功能的导管。
9月4日,“许小”在评论区写道:“患者原本花3,000元就能在局麻下解决问题,现在全麻至少8,000元起,受罪时间更长。而且劣质导管不防逆流,极易导致颅内感染,治疗费用至少多花3万元。”
他还提到,自己在值班时曾因无合格导管可用,只能建议患者转院,但其它医院的做法同样是全麻加劣质导管,令医患双方无可奈何。
湖北一名在法国驻华医疗器械企业工作的销售人员钟女士9月5日者表示,目前,许多医院已停止与该公司进行医疗设备与器械交易:“从去年到现在,我们和同仁医院谈好的项目,如今搁置不谈了,理由是不准再进口,只能用国产的。但国产器械哪有法国的先进?”
钟女士指出,中方突然停止采购外国产品,导致许多在华医疗企业大规模裁员:“我们公司裁了很多人,销售人员裁掉了八成。”
据财联社7月7日报导,自7月6日起,政府采购医疗器械项目将执行新的限制规定:医疗器械采购金额不得超过项目合同总金额的50%。
若仅有欧盟进口产品能够满足需求,则上述措施不适用。在该通知生效之前已发布中标或成交结果公告的项目,可继续签订合同,不受新规影响。
业内认为,受该政策影响较大的主要是一些高端医疗器械,例如人工脏器及功能辅助装置、体外循环设备,以及部分高端介入和植入类高值耗材这三个品类。
“许小”还披露,在另一台脑血肿手术中,他因没有立体定向引流管而一度陷入困境,最终依靠科室仅存的一根库存才勉强完成手术。
他无奈感叹称:“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医生真是活该!”
不仅神经外科耗材如此,更多进口药品与医疗器械也正在医院中消失。部分医生和患者表示,过去依赖的高端产品陆续被低价替代品取代,质量与安全风险随之上升。
中国医疗自媒体“健识局”早在去年就曾报导,国际知名骨科设备制造商捷迈邦美(Zimmer Biomet)因多款产品在中国脊柱集采中失利,计划将旗下脊柱业务全面撤出中国。这意味着未来相关进口产品在大陆市场将越来越难以见到。
医疗专家指出,中国医疗体系近年来大力推行集采与医保控费。在实际操作中,一些高质量进口耗材被排除在外,医院迫于成本压力只得停用,临床医生被迫采用替代品。
短期内虽然降低了单个器械费用,但最终导致患者付出更高的经济成本与健康代价。
上海居民陈先生对记者抱怨说:“看病越来越难,药物质量越来越差。现在普通老百姓根本看不起病。前几天我感冒发烧去医院,虽然有医保,但医院让我做了全面检查,自费部分还花了1,300元,其中大部分是检查费。”
业内人士担忧,如果当局对进口药、医疗器械和手术耗材的限制不解除,长期下去,中国部分外科手术将可能出现“开倒车”,高端医疗水平被迫下降。
点评
宏大叙事们是不是以为自己不会得病啊。
|
本帖子中包含更多资源
您需要 登录 才可以下载或查看,没有账号?立即注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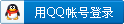
x
|
 |小黑屋|手机版|Archiver|机械荟萃山庄
( 辽ICP备16011317号-1 )
|小黑屋|手机版|Archiver|机械荟萃山庄
( 辽ICP备16011317号-1 )